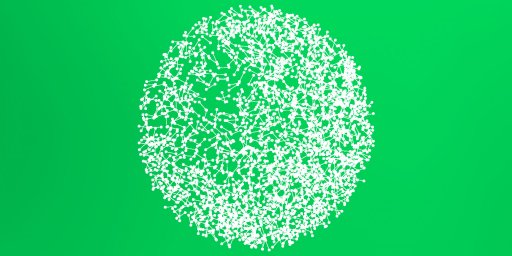该系列的开发是为了 流亡中的科学倡议,并将以项目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参与该倡议的其他学者为特色。 其目的是为流离失所的科学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分享他们的第一手经验,并提高对难民、面临风险和流离失所的学者所面临问题的认识。
您可以通过在您选择的播客平台上关注 ISC Presents 或访问 ISC 呈现.
在该系列的第一集中,我们听到了来自叙利亚,现居住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分子生物医学博士学者 Feras Kharrat 的讲话。 费拉斯分享了他离开叙利亚继续在国外学习的故事,并深入了解了在动荡时期进行科学研究的挑战。
成绩单
菲拉斯:对于那个版本的叙利亚菲拉斯,我想说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颗非常勇敢的心,你知道吗? 一颗非常勇敢的心,在战争中生活在那里,在战争中呆在那里,所有的战争岁月。 承担所有这些风险并不容易。
Husam:我是 Husam Ibrahim,今天的主持人,这是流放中的科学播客。 在这个系列中,我们深入了解流亡科学家的生活,并讨论如何跨越国界保护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该播客是世界科学院、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学院间合作组织正在进行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科学家项目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来自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的叙利亚分子生物医学博士学者 Feras Kharrat。 Feras 于 2017 年与妻子和孩子从叙利亚搬到意大利,以逃避战争并继续他的研究。 他在叙利亚阿勒颇大学完成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此期间,他的国家遭受了战争的打击。
Feras:从 2012 年开始,2012 年年中。到 2012 年底,这座城市完全是一个可怕的城市。 留在那里真的很困难也很冒险。 战争迅速将这个国家带入了一条黑暗的道路,一条非常黑暗的道路。 是的,我们经历了这场战争。 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将处于非常黑暗的道路上。 我不想详述细节,但战争影响了每个人,每个家庭。 如果您不是在谈论被杀或被绑架的人,那么肯定所有家庭都在遭受贫困,难以提供维持生计的基本材料。 你懂的? 真的很难形容,尤其是在2013年,15年2013号之后,发生了阿勒颇大学的问题。 你知道阿勒颇大学的炸弹。 大学意味着未来,大学生意味着未来。 你知道吗? 当你失去未来时,你会失去很多。 我们失去了很多。 作为叙利亚人,我们失去了很多。
Husam: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阿勒颇大学在 2013 年爆炸事件发生之前的情况吗?
Feras:所以,在战争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谈论大学和阿勒颇的研究。 那个时期有很多研究资金,特别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在那个时期,例如,如果你是一名博士生,你可以获得 16 到 32 或 35,000 美元的资助, 资助你的研究。 但我们的一位导师,他在大马士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大马士革大学为他的研究提供了 60,000 美元的资金。 所以,非常好的教育系统。 我在阿勒颇大学的实验室,在阿勒颇大学的生物技术中心使用的仪器,我现在在的里雅斯特大学使用一些仪器,它们处于同一水平,有些仪器处于相同水平战前更好。 一切都是新的,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特别是我的部门,叙利亚的许多研究中心都在支持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这些部门。 我们有干旱地区国际农业中心。 该研究中心是阿勒颇杰出的研究中心。 你可以说它是可比的,但他们只是在农业领域进行研究,我在欧洲的 ICGB 看到了这里的设施,我很幸运在战前在那个中心接受了一些培训。
Husam:那么,战争开始后的阿勒颇大学是什么样的?
Feras:从2012年开始,资金开始减少,减少,减少。 现在我认为我们谈论的是几美元、60 美元或 70 美元。 不知道,100块钱。 一些东西从1000到数百。 现在真的很难。 即使现在它取决于研究中心,叙利亚的一些研究中心也比其他研究中心要好,尤其是在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是首都,他们没有像阿勒颇那样受到严重影响。 当我在阿勒颇时,我们依靠其他解决方案,因为没有电。 我记得连续几个月没有正常的电力进入城市。 所以,我们使用其他解决方案来提供电力,但它不是连续的,这对我们影响很大,尤其是像我这样进行长期实验等研究的人。 有几天,我在进行 DNA 提取和琼脂糖凝胶,最后我需要看录像机。 不管是什么实验,有时断电,我失去了实验,我失去了实验的钱,实验的结果,我需要重新开始。 叙利亚的大部分机场都关闭了,有时你从黎巴嫩订购材料到叙利亚,这样工作并不容易。 尤其是谈到我的领域,我们使用有价值的材料和昂贵的材料,对不同条件、温度高度敏感的材料……你知道要执行——怎么说——维持相同水平的研究并不容易。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要知道,13 年 2011 月 13 日,一些澳大利亚大学来到叙利亚,他们正在为……提供奖学金,他们已经为一些叙利亚学生提供了奖学金,这是战前的 XNUMX 月 XNUMX 日。 因此,我们甚至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大学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 现在,不幸的是,它完全丢失了。
Husam: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离开叙利亚继续在国外做科学家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Feras:我是在 2015 年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我快要读完硕士的时候,我决定去叙利亚攻读博士学位。 你知道,从那一点开始,但我会谈谈我的经历。 当时的大多数奖学金以及类型,在欧洲或美国或叙利亚以外的一般开放的职位。 你知道最后他们会问你,例如,每当你想去另一所大学时,他们会问你的雅思证书在哪里,你的托福证书在哪里,而我们在叙利亚没有这些中心。 叙利亚的托福中心是托福纸笔考试,在许多大学中没有得到认可。 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你在叙利亚,你不能做这个测试——对于生活在叙利亚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谈到成本:200美元。 那时的 200 美元意味着我三个月的工资。 所以,对于大多数叙利亚人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问题,直到我有机会感谢其中一个组织,他们支持我,CARA——风险学者委员会——我想向他们表示感谢。 去旅行,做这些证明,你会有很多风险,因为路上有很多检查站,有被绑架的风险。 不幸的是,这发生在叙利亚,直到有一条完全安全的旅行道路,我才能旅行。 我在黎巴嫩考了雅思,我花了 17 个小时才到达贝鲁特,又花了 17 个小时才回来,在我们到达阿勒颇之前,道路被切断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狙击手袭击了道路,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完成这条路。 这是可怕的,可怕的回忆。 你懂的?
Husam:那么,是什么让你决定成为一名科学家? 这是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的家人想让你做的事情?
Feras:不,这是我从零开始就想做的事情。 当我在高中时,我的分数和成绩都非常高,我能够在叙利亚学习任何我想学习的东西。 但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因为我喜欢遗传学、分子医学。 这是新的东西,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时期是这样想的,当时我 18 岁。现在,我 32 岁。所以,我说的是 14 年前的事情。 我认为这门科学将成为未来的语言,考虑到我想完成它直到最后,我的意思是直到获得博士学位,从头到尾一直走下去。 我也是初中第一名,全国第一。 我有机会学习任何我想学习的东西,但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在叙利亚也是新的,而且不知何故已经很成熟了。 与德国的大学、法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以及阿勒颇大学进行了许多合作,以支持这些部门,即新部门。
Husam:现在你在意大利生活和工作,如果有的话,你定义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那会是难民科学家、展示科学家还是流亡科学家?
Feras: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首先描述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叙利亚人。 90% 不幸的是,现在在叙利亚的 XNUMX% 的叙利亚人处于全球贫困线以下。 叙利亚是当今现代最严重的灾难,你知道吗? 不幸的是,这是事实。 所以,我们所有人,所有叙利亚人,叙利亚科学家,还有叙利亚人,他们都被流放了,但这不是我们选择的。 这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这不是自愿的。 您可以在这一点下描述我的情况。
因此,叙利亚的每个人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 老实说,谁有机会离开战争,谁就接受了。 当我来到这里时,我获得了 ICGB 的奖学金。 我拿了它,但现在以现在的状态,我不能回去了。 我正常来这里,持有普通签证,我的意思是,普通电话,我的意思是,没有这个奖学金,这对叙利亚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电话。 不,这完全是一般性的竞争性奖学金,我之所以获得这个奖学金,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很好的项目,我考过雅思,我之前考过托福。 所以,我有,你可以说,获得奖学金的要求,但目前我不能回去。 这就是当前的观点。
由于我不能回去,你可以认为我已经连续离开叙利亚超过4年没有任何访问。 那不是自愿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来到这里并留在这里而不是回来。 不,因为我不能回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要知道,当我在第一批高材生中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才有自己的位置。 当然,如果叙利亚没有战争,我会回来并利用这个职位的好处,拥有自己的研究小组、自己的实验室、自己的人脉,以及与我本应成为的大学的良好关系致力于。 我想有一天回来,但你知道,我不能回来。 战争仍然存在,你知道如何回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和家人一起,和我的家人一起。 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你知道,在阿勒颇并不容易。
Husam:四年前离开叙利亚时,你还记得哪些想法和记忆?
Feras:我觉得我做了很多。 真的,我做了很多。 我为我的家人和我的未来做了很多。 我记得我父亲和我兄弟的脸,当他们告诉我去寻找你的未来时。 你有资格,你有成为科学家的动力。 所以,去寻找你的未来吧。 在飞机上,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祈祷有一天能回到叙利亚。 老实说,我一直在祈祷战争停止,不要死于叙利亚。 我想死在我的国家。 你知道,那是我的祈祷。
很难,你知道,连续4年,没有希望回来——叙利亚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 情况不好,很难。
幸运的是,现在有了互联网。 有时我可以——有时会被切断,没关系——至少每隔一周或两周和我父亲谈谈一次。 是的,很好。 但是你知道,当你在那里时,它会好得多。
谈到我的女儿们,她们不知道叙利亚是什么。 她不知道叙利亚是什么意思。 她了解意大利,仅此而已。 她来到这里,八个月大,意大利语说得比阿拉伯语好。
但是对于作为父亲的你来说,让你的孩子知道叙利亚的意义是件好事。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归根结底他们是叙利亚人。 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年幼的孩子,他们的成长与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家乡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整个欧洲叙利亚人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作为父亲考虑的另一件事。
Husam:你在意大利工作的经历如何? 您在工作场所是否因叙利亚人或中东人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
Feras:嗯,我来到了ICGB,ICGB的环境是国际化的环境,你知道吗? 在来自中东的国际环境中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你知道,有时你可能会面对一些人。 他们低估了你的技能,正如我告诉你的,你必须努力工作并向他们展示——不,我比你对我的看法要好。 而且,你知道,在研究中,不仅仅是为了工作和展示你的工作做得很好,这是关键。 你不能说这就像一个普遍的规则,所有的人都低估了你。 不,一般规则是人们热情好客的国际环境,我很高兴在那里。
Husam:那么,Feras,您积极支持国际科学组织的“流亡科学”倡议。 你参加了他们的研讨会并介绍了叙利亚科学家在他们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你开始了关于组织如何在叙利亚保护科学的对话。 您认为国际组织与叙利亚人实际合作以帮助他们重建国家有多重要?
Feras:现在,90% 的叙利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我们需要专注于让我们团结一致的事情。 我们需要再次重建叙利亚。 科学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之一。 你知道,我们对科学有很多动力。 我的意思是,谈到我自己和其他叙利亚科学家,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国家负有更多责任,你知道,当我们需要非常有资格重建这个国家时。 为此,我们需要组织的支持,而不是让我们住在这里,住在这里,住——不——有资格,有资格进入重建。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我的国家,与我的学生、我的朋友和大家分享我在这里获得的知识、我在这里获得的经验、分享我的利益、分享我的经验!
Husam:谢谢你,Feras,参加这一集并与 Science International 分享你的故事。
该播客是正在进行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科学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名为“流亡中的科学”。 它由国际科学组织运营,这是一项由三个全球科学组织在科学政策前沿开展合作的倡议。 它们是国际科学理事会、世界科学院和学院间伙伴关系 (IAP)
有关流亡科学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ouncil.science/scienceinexile.
我们的客人提供的信息、意见和建议不一定反映科学国际的价值观和信念。

费拉斯·哈拉特
Ferras Kharrat 是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临床营养和代谢组的分子生物医学博士学者,以及的里雅斯特国际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 (ICGEB) 分子心脏病学组的前研究员,以及学术和阿勒颇大学生物技术系教学人员。 Feras Kharrat 于 2012 年获得生物技术工程学士学位,并于 2013 年 2016 月在其本国大学获得学术职位。 他于2017年获得生物技术工程硕士学位,并于XNUMX年XNUMX月获得ICGEB奖学金后来到意大利,开始ICGEB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之间的分子生物医学博士研究。 他的研究重点是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并揭示不同化合物在改善衰老相关疾病症状中的作用,特别是对 Ghrelin 轴感兴趣,此外还发现了代谢相关并发症(如代谢综合征)的新生物标志物,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风险因素。
免责声明
我们的客人提供的信息、意见和建议是个人贡献者的信息、意见和建议,并不一定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 科学国际,一项汇集了三个国际科学组织的顶级代表的倡议:国际科学理事会 (ISC)、跨学院合作伙伴关系 (IAP) 和世界科学院 (UNESCO-TW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