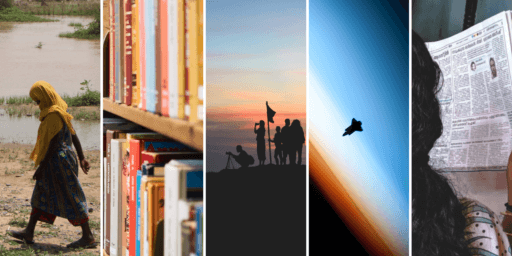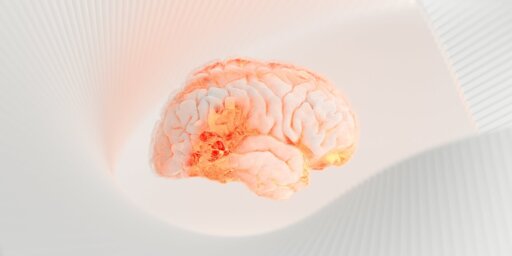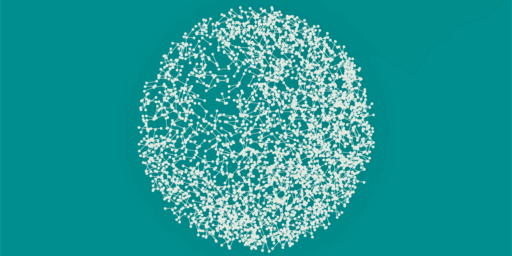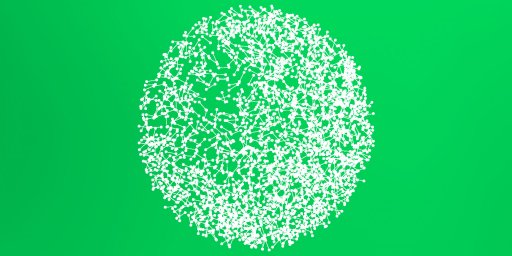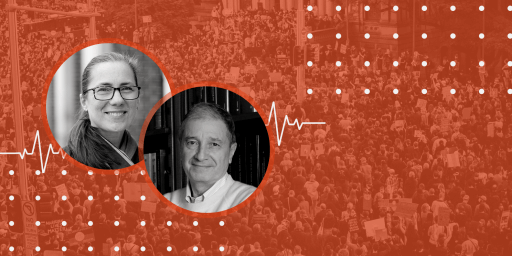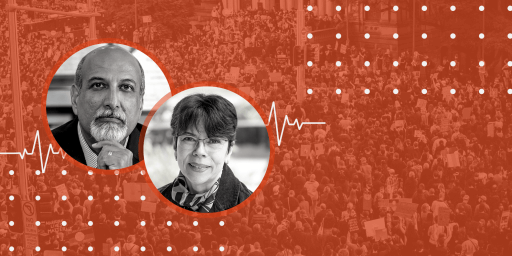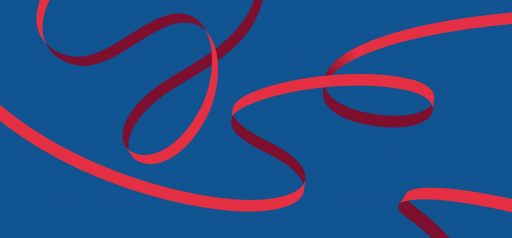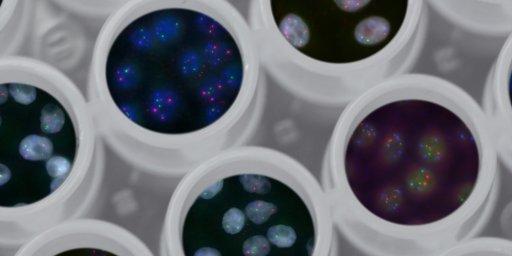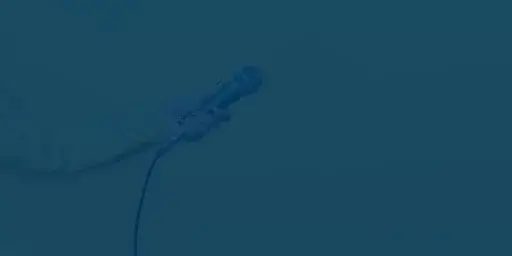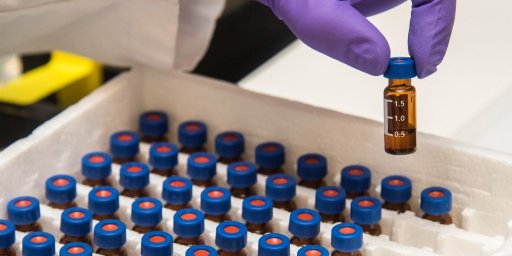联合国难民署 报告说有 6.1 百万乌克兰难民逃离 俄罗斯入侵后的国家。 更多的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门的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和机构迅速做出反应,并动员起来提供即时支持。 15 年 2022 月 XNUMX 日举行的在线会议进一步探讨了他们现在可以采取的紧急行动,以及他们在支持和重建乌克兰高等教育、研发部门以及加强关系的中长期行动中的作用在欧洲范围内。
该会议由 ISC 与 乌克兰科学, 所有欧洲学院 (ALLEA)及 克里斯蒂安尼亚大学学院, 挪威召集了全球 200 多个利益相关者,讨论最佳实践并为维持和扩展国内和国际研究合作提出建议。 会议的成果将是一份报告,旨在保护现有的 - 并重建受损的 - 教育和研究系统和基础设施。
作为会议的主旨发言人,Peter Gluckman 指出了动员科学界在人道主义响应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性,不仅要保护学者和研究人员,还要保护他们的发现、知识和对科学的贡献。
阅读 Peter Gluckman 在会议上的讲话:
“乌克兰的身份、公民、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科学的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生存危机。 但这是一场具有更广泛存在意义的危机。 现在可能已经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地缘战略分歧不仅对地缘战略事项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包括可持续性在内的全球公域的关键议程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潜力是真实存在的。
COVID-19、冲突和气候变化都会产生重叠的后果,虽然本次会议的重点是乌克兰科学和教育的未来,但我们也必须关注更广泛的教训。
首先让我说,我来自新西兰,因此深入探讨欧洲应如何应对的细节对我来说是傲慢的,但作为国际科学理事会主席,有很多要评论和反思的地方。
ISC 是世界上主要的科学非政府组织,将包括国家科学院和学科机构在内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组织聚集在一起,专注于科学。 理事会的作用是成为多边体系接口的代言人,并促进其对科学的全球发言权,承认科学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
大约四年前,ISC 由前身自然和社会科学伞式组织合并而成。 其前身组织在上次冷战中在支持第二轨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包括一些显着的成就——它的活动最终促成了《南极条约》,这仍然是国际协议中科学外交的缩影,它是 2 年菲拉赫会议的共同发起者,在该会议上,科学家们坚持多边政府间应对全球变暖需要,这直接导致了大约三年后 IPCC 的成立。 ISC 支持许多全球活动,包括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 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从冲突一开始,ISC就面临一个挑战:除了谴责入侵和随后的暴行之外,我们是否应该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科学家排除在科学界之外? 我们最初的反应很明确——我们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但我们的义务是保护全球科学的声音。 我们与我们的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磋商(财务报告准则) 我与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其他国际科学组织领导人和科学外交官进行了广泛的非正式讨论,我们认为,尽管我们谴责入侵和暴行,但这将是灾难性的长期分裂全球科学界。
就像第一次冷战一样,科学将再次成为未来第二轨关系重建的关键组成部分。 重要的是,如果全球科学界脱节,数据共享和科学合作的更大妥协可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风险,任何人都无法承受这种风险。 也许这对于科学的作用可能有点幼稚和乐观,但我们都明白,全球公域面临的许多挑战既需要新科学,也需要正确应用现有科学知识。
然而,尽管我们了解科学的关键作用,但自相矛盾的是,在过去十年中,科学变得更具挑战性,更加政治化,因为接受否认科学知识已成为某些地方党派关系的标志,而虚假信息和被操纵的知识是现在是国内和多边政治空间的核心。 悖论更进一步; 战争的核心不仅是一场人类冲突,也是一场技术竞争。 因此,作为技术基础的科学是引发冲突的一个因素。
这种关于科学和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的固有悖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了自第一个石器时代以来开发的几乎所有技术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用途。 当前关于混合威胁和双重用途科学的辩论突出了这一观点。 但鉴于任何技术都可能被滥用,我们物种面临的核心挑战仍然是定义能够确保社会明智地使用科学的治理和监管形式。 这个挑战仍然非常严峻,也是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关注的问题,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许多发达国家对许多国家并未公开批评俄罗斯感到有些惊讶。 这种立场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反应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欧洲的冲突被认为比其他地方更重要。 非洲、亚洲、中东和中美洲的许多其他冲突呢?
这值得深思,因为太多的科学也经常被放在类似的角度。 即使研究扩展到全球南方——通常被认为是为了全球北方合作伙伴的利益而不是为全球南方。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科学去殖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看法被放大了:这个措辞受到很多政治化和误解,但仍然表明,如果科学要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善,它必须清楚地由和执行与所有社会。 科学是一种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或社会的全球语言,即使它被某些人滥用。
随着世界进入一个更加支离破碎的地缘政治框架,科学必须努力建立和维护全球框架,而不是陷入极端的民族主义。 这很难,科学家是他们国家的公民,因此有义务作为公民。 但科学必须是在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全球挑战中前进的基础。 这就是 ISC 继续具有包容性而非分裂性的原因。
困境是我们希望科学不受这些现实政治问题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 科学一直具有政治维度,现代战争本身反映了科学技术被滥用于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需要务实的方法。
很明显,共享与国防和安全技术相关的知识总是存在一些界限。 但有了这种清晰的理解和附带条件,科学关系通常不会被用作政治武器。 但是,美国和中国等国家之间越来越多的科学关系开始受到政治关注,甚至不敏感的科学关系也受到质疑。 为应对乌克兰战争,各种机构和国家实施了广泛而无针对性的各种形式的科学制裁。 这些都是生硬的工具,会长期损害科学,但尚不清楚它们是否具有制裁效果。
我们还不知道乌克兰的未来将如何展开。 我希望它将以代表其公民愿望的形式出现,但我们离那个理想的未来还很遥远。 这仍然是一个激烈冲突的时期,那里有许多流离失所者——许多人作为难民流离失所,但还有许多人留在乌克兰,但由于他们应征参战而失去了他们的传统角色。
因此,我们必须解决几个不同的乌克兰科学家和学生群体的需求。 有些人流离失所,但希望尽快回到重建的乌克兰科学体系。 但是“很快”会持续多久,在什么时候有些人会放弃并成为第二组的成员:前乌克兰人希望在其他地方永久重建他们的生活,第三,还有一些仍在乌克兰的人试图在破坏较少的地区维持生计某种持续的活动。 这些团体中的每一个都需要不同的支持和帮助,ISC 已资助一名协调员与他们合作 风险学者, 联合国难民署 和其他人协助联合响应。
我强调协调的必要性。 每个人都希望被视为提供帮助,但当多个团体以不协调的方式行事时,它就变得无济于事,我呼吁双方同意并遵循协调援助机制。 这不应该是团体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美德信号来利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好地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有组织的合作。
希望在重建阶段有机会在乌克兰科学家和世界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之间建立大量新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建立全球知识网络,该网络必须成为我所说的第二轨道多边主义的核心——我稍后会详细介绍。
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一群主要学院与乌克兰科学院一起发布了一项 10 点计划,以解决来自乌克兰的流离失所科学家最明显的援助需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重建援助。 我不会详述该宣言中提出的观点,因为它们显示了令人信服的道德和常识。 但他们强调了困难——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一个已经读了 3 年博士的学生,她的所有数据或实验支持都丢失了,她必须重新开始吗? 那个职业生涯中断了 2 年的年轻人怎么办——他们会一直被视为二流科学家吗?我们如何处理科学数据和报告,完成了 80% 的工作,但可能永远不会完成? 我们如何在认识到必须保持科学完整性的同时记录这些努力和贡献? 重建科学体系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你是从相同的机构重新开始,还是这是一个从一些更成功的国家汲取思想做出重大转变的机会? 在悲剧中也有机会,这需要反思可以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重建的系统,很可能比以前更与欧洲联系在一起。
但在我继续之前,让我再谈谈乌克兰,我担心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它反映了我的地震经历。 至少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对科学和教育基础设施的破坏是巨大的。 其中一些地区在过去 19 年也受到 COVID-2 封锁的影响,这意味着教育和研究的中断不仅是自 19 月以来,而且是在另外两年的中断之上堆积起来的。 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度反思的维度。 全球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迅速上升。 在 COVID-18 发生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由于复杂的原因,在过去十年中,许多国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受损率翻了一番或更多。 在经历了 3 个月的连续地震(包括 6 次相隔大约 2011 个月的新西兰基督城市的大地震)之后,需要的心理健康支持翻了一番,而且十年后的需求仍远高于基线水平。 创伤后应激障碍在高中生、大学生及其他学生中很常见,这将在几年内产生影响。 我提到,因为恢复通常被认为是机构和基础设施的物理恢复,但正如我在 XNUMX 年向新西兰政府建议的那样,只有当人们感到他们恢复了自主权和自主权时,恢复才算完成。 在比自然灾害更复杂的冲突中。
因此,现在让我扩展讨论并进行概括。 有很多方式可以破坏科学——战争、流行病、自然灾害。 中断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设备或试剂的供应线中断、基础设施损失、资金损失。 但是,随着我们面临更多地缘战略不稳定、进一步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引发的难民危机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开始更系统地思考科学作为一项全球活动必须如何持续下去。 这是一个需要深刻反思的领域——这一悲惨事件的教训绝不能被视为短暂的。 最大的风险大多发生在科学活动已经边缘化的国家,全球北方现在必须考虑其义务,以更加系统地加强全球南方的能力和伙伴关系。
跨越国界的科学合作和科学有许多积极的属性,我不需要向这些听众重复。 但各国需要更加重视这些合作。 他们需要投资和努力。 合作的成本是资助者通常不愿承认的。 但它有好处——它创造了弹性。 在有合作的地方,学生、研究员和科学家可以找到临时住所,当他们返回可以带来设备和试剂的时候,他们会带来想法和新同事,并且可以快速重建。 跨境科学合作应成为所有国家的一项关键战略需求。
我提出这个论点还有另一个原因。 多边体系处于弱化状态; 显然,1989 年后全球化时代的热情已被日益丑陋的民族主义所取代。 民族主义干扰了对 COVID-19 的反应,灾难性地减缓了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并导致了这场冲突的出现。 存在的问题让我们眼前一亮——除了气候变化、水和粮食不安全、难民危机、流行病复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凝聚力丧失、心理健康损失率上升,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所有这些似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迫切需要考虑所需的科学。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让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对循证风险评估做出反应?
科学通过促进对共同语言的理解和使用,通过促进合作而具有间接的外交价值,而科学合作依赖于信任。 建立信任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投资于科学合作。 但科学也具有直接的外交价值——特别是,它可以支持全球公域问题的进展,确保开发出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知识。 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 ISC 在经过两年的调查后,建立了 全球可持续发展科学使命委员会 为首 伊琳娜·博科娃 和 海伦·克拉克,知道当前的资助和开展科学的系统正在留下很大的空白,并且不能很好地服务。
但科学还必须应对部分由地缘政治环境和后全球化世界的兴起所带来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科学界不能被动。 我们距离 8 年只有 2030 年的时间,距离我们在 2030 年设定目标时所拥有的更理想的 2015 年愿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必须诚实; 正式的多边第一轨外交体系在很多方面都让世界公民失望。 它在大流行期间表现不佳——正是科学家们跨越公共和私人科学的界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合作制造疫苗,而联合国系统和世卫组织的进程显然由于地缘政治而未能达到最佳状态. 正式系统在确保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方面表现不佳,因为我们继续沿着一条意味着我们将很快超过商定的 1 摄氏度上限的道路。 它让战争的残酷性在乌克兰爆发,许多其他冲突也在酝酿之中。 难民危机、饥荒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在今年 1.5 月之前就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ISC 等第二轨组织必须再次在确保更强大的全球脚手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称之为 轨道 2 多边主义. 在这种环境中,科学合作成为将摇摇欲坠的星球维系在一起的核心,并抑制了猖獗的民族主义带来的最坏影响。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选择有限。 我们决不能让这一可怕的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过去; 这是全球公域面临更大挑战的征兆。 作为一个科学界,我们要么被动,要么承认,在寻找帮助乌克兰的方法时,我们还必须概括并找到确保我们星球和人民未来的方法。
科学合作和外交在确保我们的未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ISC 将提升自己的游戏水平,以便它也能够履行这一义务。”
阅读并签署流亡科学宣言
最近发布的《流亡科学宣言》旨在帮助陷入危机的研究人员。 希望增加支持和认可宣言的组织或个人可以这样做。 立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