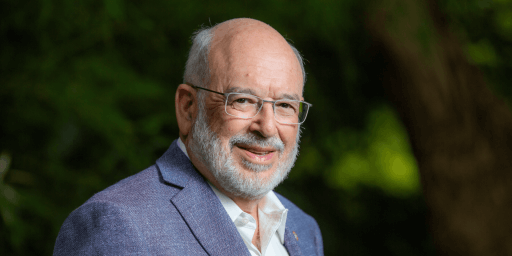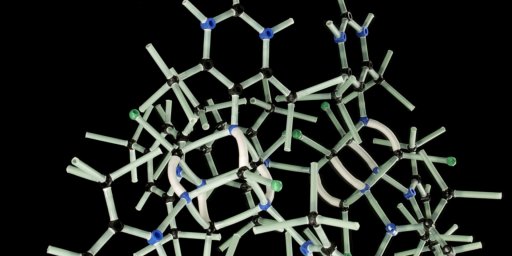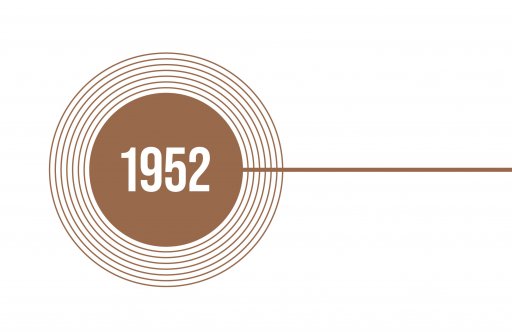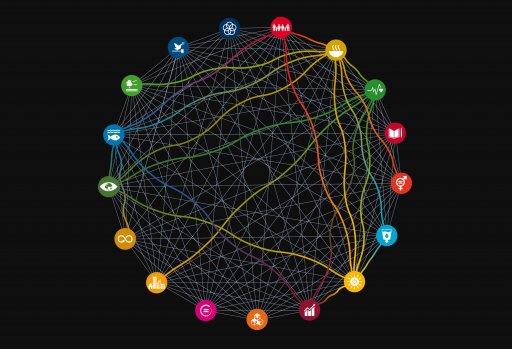关于后常态科学的辩论始于一个观察:我们生活在一个事实不确定、决策风险很高且这些决策紧迫的世界。 这对科学意味着什么?如果科学想要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这意味着什么?
萨雷维茨: 无论你在后常态问题上做什么科学,它总是不完整的,它总是会被修改,而且高度不确定。 它可以从许多科学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多项科学研究可以得出多个结果,因此它会导致大量可以代表不同价值观集的真理。 价值观和事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相互配对。
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每个人都在谈论如何就转基因生物达成共识。 嗯,围绕转基因问题的一小部分达成共识,就像围绕气候变化的一小部分达成共识一样。 但真正的问题与“可以做什么?”有关。 问题。 例如,对于转基因生物,当人们说有共识时,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它们不会带来健康风险”。 所以我会接受它的健康风险,我没有问题。 但随后你会说,“我们知道它们将成为非洲经济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吧,也许那是真的——你用的是谁的模型? 你用什么样的数据来生成它? 你的假设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多变量、开放的系统中,任何涉及对未来的预测和关于世界将如何看待的主张,都会受到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主张和结论的影响。 这正是发生的事情。
当你将科学带入政治辩论时,你 已可以选用 挑选你想使用的科学。 您必须将其与您想要解决的政策问题的特定优先级相匹配。 我认为科学真的很重要,我认为我们想要实事求是,我认为我们想要掌握现实,我认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有这么多前进道路、这么多相互竞争的价值观、系统本身如此复杂的问题,我不认为科学是解决方案的特权部分。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就应该做什么达成政治共识,那么科学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如何界定问题,人们就不会为结果争论太多。 这就是为什么处理紧急情况比处理一个长期的、旷日持久的、长期的问题要容易得多的原因。 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存在价值趋同,每个人都想解决紧急情况,而且定义非常明确。 此外,您还会收到反馈。 如果科学不好,你会发现的,对吧? 这些事情都与这些更大、更长期、更长期的问题无关。
如果您是在科学与政策之间工作的个人或组织,您将如何处理科学无法提供明确答案而政策制定者提出确切要求之间的这种不匹配?
萨雷维茨: 通过建立流程,在知识生产者和知识用户之间进行更定期的交流。 我喜欢使用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防部的这个环境研究小组。 从而成功解决了民用方面无法解决的各种环境问题。 原因是国防部没有政治化,他们非常以使命为导向,他们没有尝试委托基础研究来了解问题的所有方面,他们只是需要解决问题。 在保护濒危物种之类的事情上,我们在民用领域遇到了很多麻烦,但它们非常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科学的使用者确实占据了相同的机构环境,他们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
但这听起来有点像我只能在自己委托的决策中使用科学。
萨雷维茨: 在我的大学里,我们有一个叫做“沙漠城市决策中心”的东西。 ASU 位于沙漠中部,几乎没有下雨,有四百万人需要大量的水。 背后有很多经济利益,还有住在那里的人的生存。 我认为这个中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多年来他们与水资源管理者建立了关系。 这使他们能够保持作为学术研究人员的独立性,同时也了解水资源管理者所面临的使用环境。
另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运行一个名为 区域综合科学与评估,RISA,其想法是,对于存在自然资源问题的领域,例如水问题、土地使用问题、自然灾害问题,由政府机构资助的科学家应该与决策者合作,帮助他们进行研究议程。 再说一次,科学家们仍然是独立的,他们不在决策者办公室工作,研究也不由他们支付,但他们可以内化决策者的约束和问题的性质,并且以提供有用信息的方式进行研究。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之间的一种调和,通过彼此生活,通过相互了解。
通过更紧密的联系和更频繁的沟通。
萨雷维茨: 是的,并且持续沟通。 但我认为你关于组织是否需要为此付费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因为为了保持独立性,也许他们经常不这样做会更好。 我认为 RISA 案例和 ASU 沙漠/水案例是研究人员在政治上被孤立的例子。 他们的钱不是来自决策者,但他们确实会持续不断地相互交流。 所以我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好例子,像这样的小例子,但它们需要真正集中注意力和适当的制度结构。
那么,这也是为了将大问题更多地锚定在本地吗?
萨雷维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显然有些问题是大问题。 我认为,当事情可以在地方或区域层面上对上下文敏感时,这通常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而,很多时候科学资助流程并不是专门为此而建立的。 但我不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应用这些想法是不可能的。 例如,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思考像能源技术创新这样的问题,一个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技术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的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你仍然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工作。 比较美国和德国及其不同的能源创新方法。 所以我不认为它必须是本地的。 这取决于问题。
尽管人们认识到生活在后常态模式下,但许多人似乎仍然很难摆脱所谓的传播科学缺陷模式。 这个想法是,如果只有更好地传播科学,那么公众就会理解并改变他们的行为。 但是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这种模式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如此有弹性?
萨雷维茨: 好吧,我也应该说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会接受后正常模式。 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可能从未接触过它。 后常态科学理念确实挑战了科学作为一个单一事物的概念,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PNS 确实说我们必须在这些有争议的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科学,我不认为大多数科学家们想去那里。 赤字模型让他们负责:“我们传达事实,你倾听并采取行动。” 因此,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就不是科学的问题。 这是科学界普遍持有的一种自私的迷信。 迷信很难动摇。
同时,根据我与真正关心产生社会影响的科学家交谈的个人经验,他们只是不知道替代方案是什么。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想法。
萨雷维茨: 好吧,答案可能并不总是与科学家做某事有关。 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机构。 我认为有些事情是科学家不应该做的,那就是声称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对公众不屑一顾。 我只是认为这些事情是无益的,并强化了这种特权概念,即使个人不禁放眼世界,发现科学并不是一门连贯的东西,不能就所有这些问题说出一个真理。 因此,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我们的企业进行更多反思,对它更诚实、更谦虚,首先。
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在科学方面存在巨大的制度问题,这些问题不会由个别科学家处理。 科学界的领导者确实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加紧努力。 认真对待科学政策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加紧努力。 我实际上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停止期望个别科学家做这么多,因为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模型认为,如果每个科学家都能清楚地向世界传达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那么每个人都会理解事情,我们都会更加理性,我们的问题就会消失。
你在这里触及了一些你写过的问题 你的文章“拯救科学” 同样,关于科学系统的建立方式如何鼓励平庸、没有任何应用或完全错误的研究。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在你看来,当今科学体系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萨雷维茨: 好吧,我写了一万四千字,所以……
你能把那些减到一百吗?
萨雷维茨: 嗯,首先,科学是、可以、而且应该是免费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 我也认为这很危险,因为它导致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对科学负责只是科学界本身的内部事务,你不必对外部世界负责。 这实际上意味着您不依赖外部世界的反馈来帮助检查您所做的科学是否值得或任何好处。 所有这些低质量科学被曝光的原因之一是,你知道,我们妖魔化的工业界开始研究生物医学科学中的一些结果,他们用来尝试开发药物并且无法复制他们。 我相信,这种缺乏责任感源于这种纯粹的、绝缘的科学的理想。
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在这些大而开放的问题上正在做大量的科学工作,实际上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有意义的结果。 没有办法测试。 没有办法从真实系统中获得反馈。 在某些方面,我们提出了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对它们进行研究。 但是以不断变化的营养建议为例,你应该喝咖啡因还是不应该,你应该喝红酒还是不应该。 我认为真正的教训是,我们没有问正确的问题。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这取决于。 这是上下文的。
因此存在与隔离和内部问责相关的问题。 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关注跨科学或后常态科学问题,实际上很难说任何关于质量的事情,科学家们很容易得出看起来有意义但实际上没有意义的结果.
然后当然还有可怕的激励系统来发布,发布,发布,获得赠款,获得赠款,获得赠款。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这种系统性的积极偏见,如果你将这些激励措施与其他孤立和问责问题结合起来,你基本上就会有一个失控的系统。
您已经说过,也许我们不应该要求个别科学家改变系统。 谁能改变它?
萨雷维茨: 正确的。 非常困难。 我认为很多事情都必须发生。 正如我所说,一件事是,领导层确实需要站出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它。 政策制定者不需要将其政治化,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对吧? 资深科学家可以退后一步,他们不必像车轮上的沙鼠一样,他们可以说我不再做坏科学了。 或者我不会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 或者我将对我的结果更加谦虚,或者我将发表更少的论文。 我将停止培养尽可能多的博士生,他们以后不会找到工作。
我认为科学界可以摒弃对理想化、柏拉图式的科学概念的一些刻板印象,因为它给了我们完美的真理。 他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但这是一种方便的神话。 对企业的性质多一点诚实。 所以有很多事情将不得不发生。
然后我还想——这是我试图以我自己谦虚的方式做的事情——让我们寻找事情进展顺利的地方。 让我们都了解为什么它们运作良好,以便我们可以将其用作模型,同时也庆祝这些特殊的事情。 它们往往很小,更边缘化,通常是反文化的和违背粮食的。
我只想再一次回到你所谓的跨科学:大问题,你说也许这些不是我们应该问科学的问题,或者只问科学。 您是否认为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可能需要从正确的事情转向——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萨雷维茨: 好吧,问题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需要在政治上确立。 而且,我认为,在我们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有所了解之前,继续收集关于要做什么的事实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这些并不完全不同。 但它们并没有我们说的那么紧密。 1990 年有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好数据,表明应该做一些事情,然后人们开始谈论它。 我们不需要再有 20 年的气候模型,在此期间,实际上不确定性和政策变得越来越差,而不是越来越好,原因我现在不想谈论。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放弃的一件事,因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那就是首先我们可以让科学正确,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利害攸关的价值观。 谁是不同类型期权的潜在赢家和输家。 然后用它来代表不同类型的选项为政治辩论和知识创造提供信息,因为他们知道它们将在政治上展开斗争。 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一些事情。 但很多时候,——我的意思是政客们在这件事上完全是同谋,他们宁愿做什么,让别人做研究还是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对吧? 所以他们可以说,做研究,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科学家们可以说很棒!
我们还不知道。
萨雷维茨。 是的。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阴谋。
在您的文章中,您将大数据视为可能使科学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的东西。 每个人都把它看作是我们可以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科学发现库。
萨雷维茨: 是的。 我认为它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之类的东西非常有用,你需要无限量的地理空间数据等等。 因此,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快速反馈的技术应用,大数据非常棒。 但是对于跨科学问题,你可以深入研究数据,寻找你认为可能值得测试的因果关系,并对其进行一些统计测试,我认为我们最终会看到噪音围绕这些问题会越来越糟。 科学家们将能够在这些复杂的问题中找到更多的小真相,这些问题仍然无法形成任何特定的连贯观点。 它会让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因为它会给科学家们提供一个更大的资源库来寻找因果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 因此,除非您可以将它们的整个网络组合在一起以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
但这不是大数据的最终目标吗?
萨雷维茨: 可能是这样,但这就是所谓的拉普拉斯恶魔的最终目标,即一切事物的综合模型,但请记住,一切事物的综合模型就是事物本身。 因此,任何时候你低于这个值,你都必须做出假设。 任何时候你做出假设,你都会有偏见。 所以我们可以在某些类型的模型上做得很好,尤其是那些我们得到反馈、天气预报的模型,每天你都会发现你的预测是否好。 但是对于我们没有得到这些反馈的事情,我认为综合建模可以提供预测性和某些知识的想法是虚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