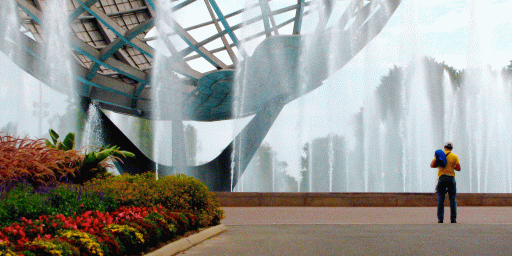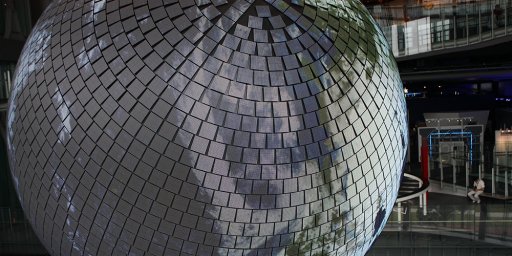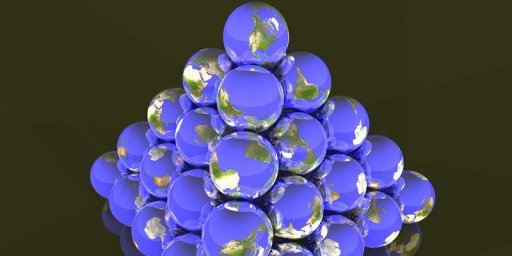考虑到当今的挑战以及您在可持续城市方面的工作,人类发展概念应从根本上包括哪些要素?
我认为最初的人类发展概念是扩大人们的自由和机会并改善他们的福祉的过程,以及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关键维度,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是从大多数人生活的环境,城市来看待这个概念。 对我来说,城市是一个为人们提供服务的系统系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人类发展的推动者。 人们从农村搬到城市的一个主要动力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城市的基本服务更好。
然而,我想区分物质服务和非物质服务。 物质服务包括住房、获取食物、水、能源和交通、废物管理和绿色空间。 人们搬到城市寻找这些类型的物质服务。 但人们也因为社会和其他非物质服务而前往城市,例如教育、工作、文化和公共安全。 教育被纳入人类发展指数,但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文化和公共安全,在最初的想法中却没有。 城市提供的服务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依赖于环境,例如能源或水。 因此,对我来说,将城市视为更大系统的关键部分也很重要。
根据将城市视为为人类发展提供基础服务的中心的想法,您是否表示添加关系维度很重要?
是的,我相信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人们被剧院、电影院和博物馆等文化和其他社会服务所吸引到城市。 社会和关系服务也非常相关,可以实现多样性,促进不同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理解。 今天在城市中发现的跨文化关系已成为许多人生活质量概念的核心。
安全也很重要。 许多人倾向于去城市,认为他们会更安全,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保护服务,他们认为这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更安全,甚至提高他们的预期寿命。 不幸的是,在许多城市,情况已不再如此,而且城市的安全性通常不如农村地区。
基于城市需要提供某些东西以促进人类发展的观点,新出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除了我们现在都知道大流行的风险是巨大的外,一个主要挑战是许多城市地区,主要是在低收入国家,居民无法获得基本服务。 太多人搬到城市中心,被提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所吸引,最终无法获得能源、水、卫生设施或废物管理。 不幸的是,缺乏这些基本服务的人数并没有以全球所需的速度减少。 在没有提供这些服务的情况下发展的城市变得非常成问题。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口总体老龄化。 比较今天和未来的人口金字塔,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接近本世纪末,大约 35% 的人口将达到 65 岁或以上。 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将在 80 岁左右,这意味着大量 80 岁以上甚至 90 岁以上的人。除非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职业生涯的长度,否则我们将有数百万人没有工作超过 XNUMX 年。 这将在收入、税收、退休养老金以及医疗和老年护理成本方面产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果。 城市应根据这一现实调整服务。
另一个挑战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移民和人员流动。 一种类型的迁移是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地区,这给城市提供的服务带来了压力,正如我之前概述的那样。 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例如普遍缺乏服务或自然资源,另一种类型的迁移是在大陆和国家之间。 由于气候变化,全球从农村到城市地区以及跨大陆的迁移在未来将极为重要。 我们需要为因极端事件增加和其他气候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人流做好准备,许多人没有应对这些影响的能力。 考虑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中心已经无法为其居民提供服务,这些增加的移民流动可能真正危及人类发展成果。
在我看来,另一个挑战是现有的不平等率。 显然,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就在几十年前,虽然世界仍然不平等,但财富创造的分配更加平等。 例如,当公司提高生产力时,工资也会上涨,人们会赚更多的钱。 但如今情况并非如此。 今天,生产力和财富创造只属于非常富有的人。 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加剧是未来几年的另一个挑战。
这将我们引向一个相关的问题,即全球安全和治理。 当不平等继续侵蚀社会结构时,人们如何参与民主进程? 人们愿意采用更激进、更不民主的制度。 我们有许多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案例,比如唐纳德·特朗普或鲍里斯·约翰逊,以及中国一个主要威权政权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 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领导人继续推进他们的议程,却忽视了人们的需求。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促进民主、公民参与和公民参与,我们如何发展制度,让人们能够以更深刻的方式参与? 对我来说,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而核心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长通常不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也不是民粹主义者,因为他们专注于解决公民面临的问题。
我们如何才能使人类发展的概念更具战略性,并将其与可持续发展更多地联系起来?
首先,让我说,我认为我们绝对应该考虑如何在衡量人类发展的方式中纳入更多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及其具体目标的要素。 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的主要问题是,这是一个与一个国家的现实无关的宏观指标——GDP可能会因为少数富人赚了很多钱而增加,但作为大多数人的身份可能会变得更糟。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在社区和人的层面使用微观指标来衡量人类发展。 如果你衡量人均 GDP 的变化,不仅是在一个地理区域汇总,而且对每个收入百分比范围进行汇总,那么结果会非常不同。 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助于将这一衡量标准分解为不同的方面。 挑战在于翻译可持续发展目标,使其反映人们的生活,并使人们能够将其与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
关于如何使人类发展更具战略性,或许我们可以借鉴欧盟委员会现在提出的使命驱动的观点。 我们需要就北极星、目标和宗旨达成一致,并为此感到兴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 SDG 17 的全部意义所在,呼吁全球社会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 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使命,而是以分散的方式在部门方面创造了孤岛。 例如,在 COVID-19 的背景下,一些城市正在考虑如何创建解决方案并咨询其他城市,这是一种 竞合,合作竞争。
这些城市网络很重要,但并不完整,因为它们通常不包括与公民或其他关键社会参与者(如私营公司或研究人员)的协商。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为政府、公民、科学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创造空间。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真正实现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使命的唯一途径。 问题是很难建立这些伙伴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信任,推动这些过程需要大量时间。 为协作创造空间与研究或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资金无关。 它是关于人们促进流程和建立信任的。
什么是对人类发展有意义且有用的定义?
对我来说,一个有意义和有用的定义必须以人为本,并以人为本。 这就是为什么 GDP 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的原因,因为它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钱而不是人。 人,他们的物质和非物质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服务,应该是定义的中心,让我补充一下,这些也应该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当前转型的中心。
在 COVID-19 危机之后需要进行的重建需要以人为本。 重建将重建经济,但这种复苏应侧重于人类发展。 我们应该开发提供上述服务并真正满足人们需求的新社区。 例如,我们可以建造所谓的“15 分钟之城”。 这个概念传达了一个城市中心,基本服务位于步行 15 分钟内,因此弱势群体无需依赖交通工具。 他们可以步行到任何地方获得食物、医疗保健以及社会和文化互动与服务。 因此,当我们考虑需要创造的变革时,让我们专注于改善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制定真正以人为本的新社会契约。

胡里奥·伦布雷拉斯 是马德里理工大学北美区主任和哈佛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图片由 Tony Hisgett 提供 Flick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