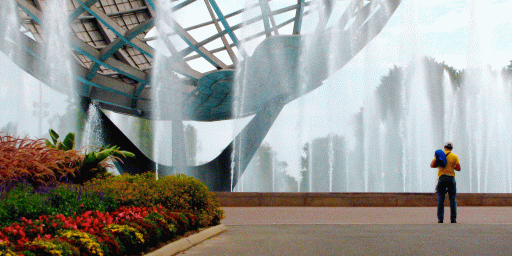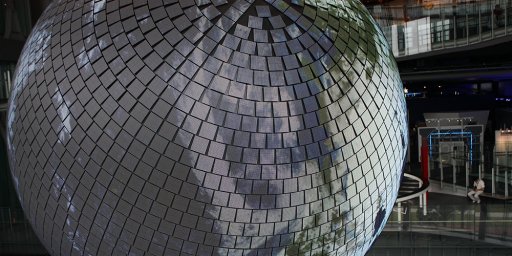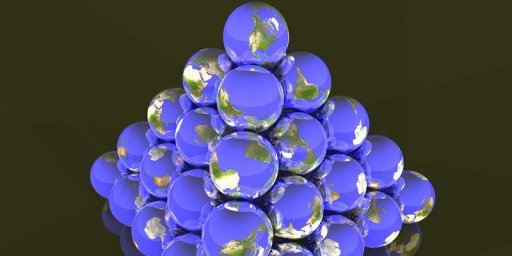您认为人类发展理念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我非常赞同玛莎·努斯鲍姆通过能力方法发展的观点,即人类发展的核心是实现人类的潜力和能力。 我要补充一点,这也是关于 社交、 能力。 我认为 Amartya Sen 和 Nussbaum 都看到了社会维度,但有时会采用能力方法,就好像这完全是关于个人实现他们的自主能力。 他们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吗? 他们能找到好工作吗? 他们能有小企业吗? 小额信贷? 但这些例子也是涉及其他人的情况,我认为没有人能完全靠自己实现人类的潜力。 此外,算作实现的东西往往是 共享社交 事情:无论我们是在谈论恋爱还是拥有家庭,或者能够开展业务,或者能够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因此,首先是从能力和潜力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确保我们从个人和社会/集体的角度来看。 第三,当我们处理能力的概念时,我会将人类发展与人类转变(因为没有更好的词)区分开来。 确实,当我们谈到要开发的人类潜力时,我们往往会认为一开始就有一些东西。 有潜力,但除此之外,还有将要发展的能力。
我认为意识到已经存在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潜力,是故事的一部分。 人类不仅 开发. 植物可以从种子发育而来; 发展的道路是完全预先确定的,如果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干旱或早霜),植物就会发展。 这对人来说并不完全正确。 路上还有很多岔路口。 但也有潜在的转变。 这在个人层面上是正确的,但在种群或社会或物种本身的层面上更是如此。
我将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想法:首先,人们在营养和更好的医疗保健方面发生了多大的身体变化,这意味着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平均身高更高。 他们可以过度改变这种变化并变得肥胖,但这并不是更好的营养,而是太多的食物。 人的转变是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
但除了物理之外,我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利用技术改变人类。 有些是人类工作时的支撑,有些是越来越复杂的假肢装置,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本质。 更进一步,基因工程是另一个潜力被转化的领域。 我们可以设计人类对某些疾病免疫。 但是,我们如何规范研究并确保公平获得和分配利益?
这表明,做人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仅是实现固定能力的问题。 它是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同样,作为个体的人会发生变化,但这些转变也是社会性的。 如果你想到语言——发明一种语言或变得识字——这是发生在个人层面的转变。 但是对于一个有文化的社会来说,大多数人都可以阅读和分享信息,这是对人类的意义和人类将拥有的能力的转变。
基于您在团结网络方面的工作,这如何符合人类发展概念?
我提到人类的发展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能力:能力的实现取决于人们之间的共享或团结。 有时这种团结是温暖、有爱心和友好的,这是我们日常的团结感; 但有时它是社会组织的问题,通过市场和企业。 在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和与之相关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依赖程度; 我们实现自己的议程或自己的可能性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人相互依赖。 我们人类能力的一部分是与他人合作、帮助他人、爱他人、与他人合作、与他人交流。
如果我们回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大革命之类的东西上,发展政治理论从那时起首先关注的是自由,其次是与平等的权衡,但往往忽略团结,即当时所谓的博爱,指的是我们合作的方式。 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式与个人自由一样重要,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对于使民主成为可能至关重要。 再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大流行带来的破坏是如何破坏这种团结的,以及我们如何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对自己来说基本的东西。
考虑到我们在地方层面和全球层面相互依存的观察,您认为有可能建立一个人类发展或人类转型的普遍概念吗?
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普遍性:人类发展不同,实现不同的能力。 以语言为例,也许一个很好的看待这一点的方法是说人类没有潜力 只是 对于一门语言,他们有潜力 语言 结果是人类会说不同的多种语言。 普遍的概念是多样性的能力,而不是相同的能力。
您如何看待这些团结网络适用于非人类?
我认为我们确实与非人类团结一致。 对许多人来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狗或猫。 但在很多方面,我们与非人类、自然和无生命的物体相互依存。 现在,我不认为团结的概念有问题,感觉我们应该与这些非人类存在一些团结; 我们是否辜负了这种团结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我们是卑鄙的老师,我们会失败吗? 如果我们不是素食主义者,我们会失败吗? 如果我们允许环境被破坏,我们会失败吗? 它为我们提出了道德问题。 就像与他人的关系对我们提出道德问题一样。 我们应该有不平等吗? 我们应该支配人吗? 你如何尊重他人?
然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大问题是关于人类有多特殊。 人类发展理念非常关注人类。 如果我们开始从社会角度考虑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开始考虑它与各种环境和其他非人类的关系。 此外,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部分潜力,即人类发展初期的能力,只存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不必说它们与我们的人际关系完全相同,就可以认识到它们是关系。
你会说这个问题的这些方面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吗?
是的,但我认为它们变得越来越突出;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的方式。 这来自不同的方向:考虑动物或非人类动物的权利; 在气候变化、地球的潜在破坏以及我们与自然本身的关系等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然。
随着医学和技术科学的变化,我们是那种自然的一部分,是整个地球的一部分,也以其他方式出现。 例如,我们体内的大多数遗传物质并不是我们独有的; 它是短暂的,随着我们体内的微生物来来去去。 这是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除了在相当具体的科学医学意义上,它并不是对人类发展意味着什么的重新思考。 然而,它确实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意义的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人类对于理解人类的重要性。
这些问题出现的学术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交叉和相遇?
他们应该比他们做的更多。 这也延伸到与其他类型知识的关系。 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专业都犯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和繁荣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罪行。 但是,在重新思考人类和重新思考整个世界的过程中,关注跨学科科学是关键。 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互联互通的必要性。
您认为这种情况会影响政策制定者利用学术知识制定政策的方式吗?
我认为有一条直接的途径可以让特定的科学知识为政策提供信息。 例如,我们了解社会对吸烟的影响模式,并将这些知识用于决策。 第二条路径是一种技术:科学首先通知的不是政策,而是技术的发展,然后提出了政策问题。 如果您考虑基因工程,即使是现在,也很少有政策制定者对其有深入的了解。 但是,为基因工程技术提供信息的科学正在推动政策制定者。
科学确实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入政策,包括改变对问题的一般认识以及对问题的理解。 例如,在大流行的背景下,科学家的作用部分是直接告知政策制定者; 可以说,这在流行病学上是一种减少病毒传播的好技术。 但这也部分是为了塑造公众的理解,气候科学就是一个显着的例子,它比决策者更快地传播到大部分公众,并产生了对决策者“倾听科学家的意见”的公众需求。 Greta Thunberg 说的。
您将如何解释这一关于气候科学的观察结果?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叙事是否更容易捕捉?
我认为这部分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追求短期到中期的近期目标,这意味着他们不会经常考虑未来一百年或人类的其他可能性。 例如,如果您的任务是编写有关在大流行期间分发口罩的规定,那么您可能会稍微注意科学。 但你主要会关注经济和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你生产和分发口罩的能力。
相反,并不是整个公众都关注科学问题,而是有一些团体这样做,他们传播它并创造参与。 公众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它会求助于政策制定者并期望他们这样做。 公众表现为民间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宗教领袖、道德领袖和其他具有强烈表达观点的人,例如记者; 公众 有很多面孔,我们看到它伴随着气候变化,伴随着大流行,有很多公众接受,但它的分布并不均匀。
不幸的是,科学的最大途径是一条相对缓慢但非常重要的途径:教育。 通过教育包括未来政策制定者在内的广泛人群,真正将科学转化为新一代教育,特别是专业人士的教育,才是最能将科学知识带入政策的过程。
关于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您对它如何改变我们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转型的理解有何看法?
第一个观察结果是,我们一直想认为大流行是一种非常短期的紧急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紧急情况意味着某些事情很紧急,现在需要我们关注。 但在其他方面,这是一个误导性的想法。 我们认为紧急情况会意外发生。 嗯,具体的大流行是出乎意料的,但是会有大流行和传染病不是; 这是可以预见的。 我们本可以做好更好的准备。
紧急情况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常短期的、集中的事件。 地震后,我们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建,我们必须照顾幸存者。 大流行是一种不同的情况:它是一种变化。 首先,我认为这场流行病的持续时间将比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决策者想象的要长。 其次,有可能再次感染和流行病成为地方病,届时它会改变我们的一般生活条件,类似于我们患有各种其他疾病的方式。 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人类转变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短期事件时,我们将回到“正常”状态。 我们将产生一些新常态。
大流行还有其他含义:它提醒我们,我们无法完全控制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可能性。 它可能会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非常复杂、大规模的相互依赖的系统中。 系统思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不仅在公众中,而且在政策制定者中; 我们倾向于隔离问题并尝试处理单独的部分。
大流行是相互依赖的一个教训:它是全球性的方式,感染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以及它与我们机构状态相互依赖的方式。 显然,医疗保健和医院已经不堪重负,但经济陷入危机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杠杆; 不仅仅是就业,还有金融、机构、信贷和股票市场。 所有这些都鼓励了一种相互依存的感觉。 我们在思考这种相互依存感方面做得如何是不确定的,但这是一个人类发展问题,因为我们要么以非常个人主义的、单独的术语来思考人类发展,要么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和可能性有多大与他人相互依存。
您想涵盖任何其他方面吗?
我们讨论了彼此相关的不同学术领域、不同研究专业,并更好地理解了人类的转变。 我们还讨论了大流行应如何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之间的联系更加连续。 这场流行病显然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治疗药物问题,无论这对理解它有多重要。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的混合体。

克雷格·卡尔霍恩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科学教授。 此前,他曾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院长、伯格鲁恩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 他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并在那里创立了公共知识研究所。 他的书包括: 非神非帝:学生与中国民主斗争, 国家事务, 激进主义的根源及 资本主义有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