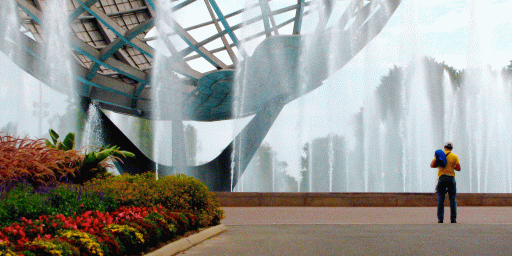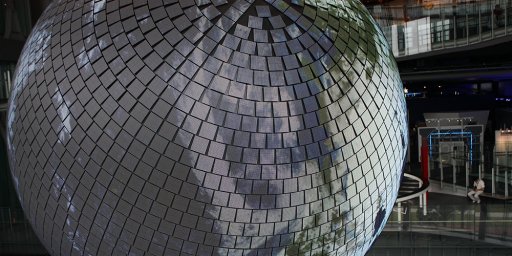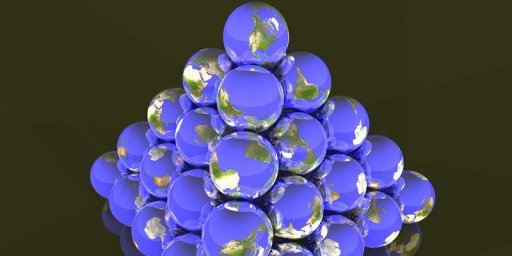您认为人类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什么?
有一幅 2015 年的 Patrick Chappatte 动画片,其中两个年轻人走过一个大广告牌,广告牌上的目标早于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其中一个年轻人转向另一个说:“我每天都有相同的目标”。 对我来说,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意义所在。 SDGs 并不完美,但它们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计划:它是最广泛咨询的,我认为很多目标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目标。 人类发展就是将这些目标放在广告牌上,并弄清楚它们在这两个年轻人生活中的样子。 矛盾的是,我认为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仍然在广告牌上,而不是在实地。 报告中的指标仍然是相对宏观和物质主义的,而不是抱负的,它们不一定能告诉我们什么真正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就是我认为人类发展的意义所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它们经常相互冲突。 看看 COVID-19,很明显每个人都想要可持续的生计和可持续的健康,但如果他们去工作以维持这种生计,他们可能会生病(感染 COVID-19)。 有必要弄清楚如何平衡这些目标。 我们在生活“或”生计之间陷入两难境地,而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平衡并不容易。
我认为最终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更好地理解它们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之间取得更好平衡的途径在于直接询问人们。 我/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关于可持续生计的,通常是要求人们绘制出他们日常生计的哪些方面适用于 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您认为我们今天拥有的不同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多维贫困指数、幸福和福祉指数)可以补充 SDGs 的指标吗?
我真的很喜欢 HDI 和 MPI 背后的想法,它超越了纯粹的经济方面,并将方法扩展到包括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和电力供应等方面。 与此同时,这些维度通常被用作标准,尽管它们相对人口和物质主义。 反过来,幸福和幸福指数更加主观和相关。 目前,这两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分开。 然而,这两者肯定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如果一个人有电和上学,并且预期寿命不错,那么幸福指数和幸福指数也可能会上升。 因此,我认为将 HDI 和 MPI 作为标准可能是错误的方法。 它们更像是一些通往幸福的物质手段。 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物质指数的得分如何与更主观的幸福感和幸福感维度以及所有其他旨在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广告牌上所说的内容转化为街头水平的指标共同变化。
您认为 COVID-19 的情况会改变还是已经改变了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
是的。 它已经改变了它,我们不会回去。 例如,在生计领域,整个部门都面临重大威胁。 围绕新自由主义议程存在重大问题。 关于体面工资的辩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辩论,因为有人类的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成本。 理解这一点的务实和合乎道德的方法是研究如何从先前的工作条件(例如缺乏生活工资)预测工作/生活的日常质量以及(无法)承受 COVID-19 等冲击的能力(参见例如,项目 GLOW(全球生活组织工资))。 否则,整个体面劳动议程 (SDG-8) 仍然非常抽象(在广告牌上)。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很多研究证据系统地跟踪这两个变量(日常工作条件,如工资和工作/生活质量)的变化如何以可预测的关系在经验上相互匹配。
回到上一个问题,我认为扩大人类发展的定义以摆脱纯粹的货币指标很重要。 在 COVID-19 之前,我们的就业水平相对较高,但主要从事脆弱和不稳定的工作。 在 COVID-19 之后,失业率较高,着眼于支持性收入仍然非常重要,但不是 标准 – 这是我们通常放置的地方 – 但作为 预测因子 其他维度的变量。 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书中 自由发展 解释说工资和收入本身不是目的,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这个想法是,如果人们以任何形式获得体面的收入,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为破坏者,COVID-19 的挑战是找到创新的方法来使人类自由蓬勃发展。 这可能包括重新审视诸如普遍基本收入(UBI)之类的激进政策选择。
我们希望与您讨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跨学科和跨部门的政策制定和规划:您对此有何看法? 您自己从事不同学科的工作吗?
我在学术系统中工作,所以我生活在思想的世界里,而且如你所知,大多数在学术界,你有自己的期刊和奖项的单一学科。 如果跨学科,在晋升和任期方面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激励措施还没有。 然而,我对即将出现的新的可持续发展期刊感到鼓舞,我们已经开始在其中发表文章。 尽管经济学话语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我的心理学专业仍有一席之地。 行为经济学是同样的物质话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不太确定这是了解人们实际韧性的正确方法。 如果他们在危险时期不储蓄,这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正确思考或未提前计划,而是因为经济需要支配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会在他们的家庭中为他们的家人做必要的事情等等。
我认为跨学科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生活工资研究中,我们与员工关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合作。 我想更多地从事公共卫生工作; 当前的流行病非常强烈地提醒人们,卫生、社区、文化和经济系统是高度相互关联的。
我是美国心理学会 (APA) 期刊的编辑 心理学的国际视野,并且我们正试图摆脱传统的心理学文章,例如转向政策简报。 在这方面,它的使命非常接近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化为人们的眼睛。 所以这种心理学有机会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
您对新西兰将知识和证据与政策制定联系起来有何看法?
在我工作的期刊中,我们现在鼓励作者提交政策简报,因为传统期刊文章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不是很友好。 我们鼓励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将研究转化为可口的政策格式。 我们有很多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提供,但其中大部分都没有进入政策。 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训练人们有说服力。 研究人员尤其可以致力于开发新的外交:您如何将证据用于现代世界的实践和政策? 你怎么能进房间? 您如何说服决策者接受证据库中的内容? 当像公司这样的组织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对整个地球,当然对社区来说都是危险的事情时,你怎么能把它们叫出来呢? 我在我的硕士课程中教授这些方面的一些方面,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关于公司和国家报告系统的指导方针,并跟踪我们通过 OECD 网络听到的一些故事。 我认为这些“新外交”,正如社会经济发展中心 (CSEND) 所说的那样,是关于让系统通过证据来负责。
我希望在这里解决 COVID-19 的一个相关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的安全性(例如,参见 Project SAFE(面向所有人的安全评估)). 我们对联合国安全方法的最后一次重大贡献是在 1994 年的《人类安全报告》中。 例如,这份报告没有涉及网络安全,但方法是确定通过指标衡量哪些因素使人们感到不安全的方法。 应用到 COVID-19 的当前情况,建立粮食安全措施会很有用,例如:人们囤积食物是因为他们对粮食安全感到害怕吗? 此外,重要的是要强调这是一个“运行政策”问题; 在冲击和危机时期,我们需要方法来应对迅速发生的变化。
有时这些灾难是人为的——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新型的人畜共患病毒是人为的灾难,是由于贪婪地侵入自然环境和生物圈造成的。 看看仙台框架,我们知道预防可以帮助人们度过危机。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我强烈支持联合国关于人类发展等式的人类安全方面的最新情况。

斯图尔特·卡尔 新西兰梅西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他的著作包括援助心理学、心理学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与工作文化、贫困与心理学、援助三角和全球流动心理学。
封面图片:由 Artistlike 提供 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