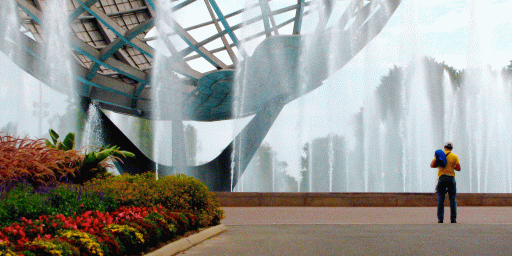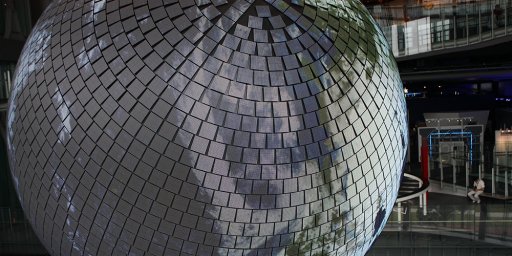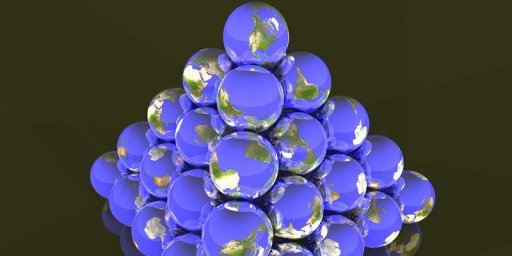我们如何重新思考我们对人类发展的概念性理解?
为了将人类发展概念化,让我从哲学家保罗的精彩格言说起 里库尔,“在公正的机构中与他人并为他人过上美好生活的目标。” 我将用四个术语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表达了“美好生活”(健康长寿、体面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教育水平),但也许应该增加更多关于幸福的指标。
其次,“与他人一起”生活意味着您无法在邻居和同胞挨饿的情况下生活。 这里的不平等问题是中心问题。 与他人一起生活还意味着根据多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范式,承认他们的身份,à la Axel Honneth,以及他们的种族、宗教、世俗群体和/或网络。 第三,“为他人”生活意味着遵守和弘扬爱、好客、关心和关心他人的道德规范。 第四,利科尔所说的“在公正的机构中”是指建立一个多元化和民主的制度。
人类不仅 经济人 还要不断地交换礼物。 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礼物关系和道德义务概念应该被包括研究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社会行为者考虑和加强。 例如,虽然我们谴责一些国家和社会对难民缺乏热情好客,但我们往往忘记深入挖掘城市、村庄和宗教或世俗社区的微观层面的热情好客。
重新思考建筑的重要性 异性,不仅涉及谁被视为对手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还涉及我们如何关心“对方”。 我想补充一下 Ricœur 的想法,即他者不仅是在这个时刻与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而且是后代。 这与以可再生自然的方式考虑消费有关; 这也与我们要求提高工资有关。
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最低工资、对高水平资本和财富征收重税以及“智能绿色增长”——以对新的、有吸引力的和有抱负的生活方式的渴望为动力(像经济学家一样说话) Carlota Perez)和缓慢增长的经济及其必然结果(包括廉价和低碳的公共交通,将公共服务视为投资而非负债,以及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
这种人类发展概念需要三个层面的参与。 个人层面承认人类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学品质,在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取得平衡,并能与邻居和有需要的人团结一致。 社区层面至关重要,不仅需要公民身份和人权,还需要承认政治。 当前在美国(美国)和欧洲开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这种政治的一部分:当社区承认种族不公正并反对白人至上及其殖民和奴隶制遗产(以雕像为标志)时,承认就开始了。
最后,在州一级,参与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问题。 在这方面,五位女性经济学家——Esther Duflo(2019 年诺贝尔奖)、Mariana Mazzucato、Stephanie Kelton、Carlota Perez 和 Kate Raworth——的工作受到 “金融时报”,是有帮助的,为主流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一些替代方案。 例如,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的创新案例研究中正确地指出,大部分商业创新和利润来自政府的基础研究支出,但没有任何回报来促进更大的利益。 在我居住的黎巴嫩,当地的小农不建立农业合作社就无法生存。 腐败的政党如此专注于地缘政治博弈,以至于他们无法为选民处理紧急的生存任务,而宗派投票可以抢先阻止新的社会运动参与者进入议会和行政权力。
当今世界以人为本的发展面临的主要新挑战是什么?
今天,我们有三种阻碍任何发展的现象: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冲突。
威权主义不仅仅是国家通过在社会生活中部署官僚主义和警察强制来采取不民主行动的趋势。 而是系统地取消民众的责任或参与国家决策,并将行政权力大量集中在官僚机构中。 人们可以想到与新自由主义有关的软威权主义的兴起,即对中产阶级的侵蚀——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历史、社会载体。 随着这种威权主义的出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削弱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性发展过程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垄断的“食利者”经济,其中剥削和劳动力的不稳定化是两个主要过程。
Karl Polanyi 关于人工商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研究很好地分析了这些过程。 然后,国家将发展威权治理模式,以增强其对抗民众不满情绪的力量。 在许多外围社会中,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薄弱,竞争更加激烈,而且国家也变得更加残暴。 在阿拉伯世界,一些政权,如叙利亚政权,对自己的人民简直是种族灭绝。 自叙利亚起义以来,已有不少于一百万人口死亡,其中一半人口要么是难民,要么是国内流离失所者。
在国家暴力和准军事暴力之间,我们见证了政治经济学家玛丽·卡尔多所说的“新战争”:有组织暴力的增长及其在现代后期不断变化的性质导致了更多的战争和道德堕落的加剧。 如果不解决这种威权主义,并且不仅将其分析为新/后殖民现象,而且与区域帝国的多样性以及分裂的地方精英的形成密切相关,人类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在阿拉伯世界,Kim Ghattas 在她的书中雄辩地分析了这种地方和区域动态 黑波,特别是关于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作用。
第二种现象是民粹主义——右翼或左翼。 全球不同地区有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浪潮。 在这里,我指的是有魅力的领导人与群众之间的直接政治纽带——这种纽带发生在既定的制度渠道之外,并通过领导人声称他,而且只有他代表人民而助长了反多元化。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和技术民主(缺乏哲学和原则)的真正危机中。 并非所有的民粹主义都是专制的,反之亦然; 然而,越来越多的存在联系。 Pippa Norris 和 Ronald Inglehart 的新书, 威权民粹主义, 非常引人注目。 在作者看来,在年轻一代在公民文化方面发生价值转变之后,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领导人已经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些人对最近的社会变化向多元文化世界主义持负面看法。 民粹主义对权力和话语权的控制据说植根于拉丁美洲的国家控制、美国的经济再分配、欧洲的移民和国内经济机会保护,以及东南亚的腐败和犯罪问题。
最后一个现象是冲突。 在一些地区,比如中东,冲突是由两个因素引发的:不相互交谈的不同精英阶层和薄弱的自由文化。 那些强硬的世俗主义者往往是左翼运动的一部分,这些运动反对支持伊斯兰运动的宗教人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宗教与国家关系框架。 我认为,“后世俗社会”需要被理论化为处理一些勾结和模糊长期以来分离的事物之间的界限的社会:宗教与国家、道德与政治,以及公共领域中的神圣与世俗争论。 正如阿曼多·萨尔瓦托(Armando Salvatore)所说,后世俗化通常与多种观点和实践相关联,这些观点和实践并非源于对世俗性的否定,而是源于对世俗性和世俗化的相当全面的反思性的兴起。
有时,地区势力的行为只是出于宗派原因(伊朗或沙特阿拉伯),或者为了加速殖民行为而分裂该地区(以色列通过“世纪交易”吞并西岸部分地区)。 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对出售武器比支持民主力量更感兴趣(除非这些力量与他们结盟)。 简而言之,全球所有这些小特朗普的胜利为非自由运动和独裁政权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际社会对许多国家(包括叙利亚、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反应非常温和,如果不是不存在的话。 2018年XNUMX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题为“以合作共赢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决议。 标题可能听起来不错,但该决议破坏了追究各国对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程序,取而代之的是“对话”和“合作”。 该决议以令人痛心的多数通过,将成为削弱联合国人权生态系统进程的开端。
人类发展方法如何让公众辩论和决策者了解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我认为 COVID-19 危机为使发展方法更加人性化提供了动力。 正如罗兰巴特读阿尔伯特加缪的 鼠疫 作为欧洲反纳粹主义的战斗,我们必须将 COVID-19 危机解读为对人类生存的考验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的隐喻。 我们、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民间社会行为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应该为后大流行时代做好准备,以便将这场悲剧转化为资产。
提醒您一下,1930 年代初的大萧条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危机的政治反应截然不同。 让我们以美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 1933 年至 1939 年间提出的新政为例。这是一系列计划、公共工程项目、金融改革、劳工改革和种族关系改革的实施。 相比之下,德国在其回应中用纳粹制度取代了民主。 社会学家米歇尔·维维奥卡今年 XNUMX 月在接受法国报纸采访时 解放,提醒我们,在二战后时期,法国抵抗运动创造了一个被赋予标签的行动计划 快乐时光 (幸福的日子)在 1944 年。必须说,这不仅包括一些恢复民主的政治措施,还包括以大型经济和金融机构国有化管理经济为特征的激进经济措施,以及当然还有一些社会措施——特别是大幅调整工资、重建独立工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 接下来的30年对法国来说确实是快乐的日子。 因此,现在由我们来决定我们将朝着哪个方向前进。

莎丽·哈纳菲 贝鲁特美国大学社会学教授、Idafat 编辑:阿拉伯社会学杂志(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项目主席。 他是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2018-2022)。 他最近的著作包括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生产:不可能的承诺(与 R. Arvanitis 合着)(阿拉伯语,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和英语,Routledge,2016 年),他是 2014 年 Abdelhamid Shouman 奖的获得者和 2015 年科威特社会科学奖。